Ua mai,水涨了”,斐济老人告诉我。在Kadavu集团的小野岛Vabea村的海滩后面,我们并排坐在一条上翘的小船树荫下的上翘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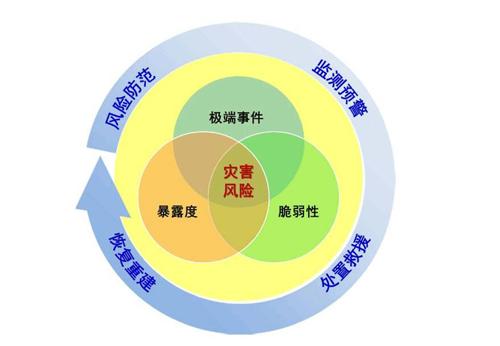
现在是2019年1月。日落将会很壮观,但我的同伴却显得很阴沉。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小野上,他目睹了沿着岛屿海岸发生的逐渐变化,他知道,海洋的崛起。
他告诉我,这里的海滩正在削减,指出沿着陆地一侧放置的椰子树干试图阻止进一步的土地流失。他担心这还不够,有一天Vabea将遭受附近Narikoso村的命运,这些日子经常在涨潮时充斥着。
他没有对科学的兴趣,他想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种事情发生,小野人可能会做些什么来激怒他,或者是否有一些魔鬼在玩耍。
我们可能对当代气候变化的原因持怀疑态度,但只有傻瓜否认其明显的影响。海洋表面无可争议地上升,证据表明世界大部分海岸线都是如此。我们对未来感到焦虑,关于我们是否可以在短期内阻止海平面上升,或者正如一些科学家所说,这是不可能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减少排放量。
在短期内,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我们向上建造房屋,人工补充海滩,我们建造自然和坚固的海防。我们希望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这种观点体现在从愤怒否认到被动祈祷的沮丧 - 恳求范围。
我们是否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面对如此深刻的关注现象?我们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海洋表面在几千年左右的时间内沿着几乎所有的世界海岸平均上升了120米。陆地大规模缩小 - 澳大利亚失去了大约23%的土地面积,现在美国的相差几乎变成了三分之一。沿海人民被迫流离失所,一些人在内陆移动,一些人在海洋中闯入,希望在地平线上找到无人居住的土地。
那些人怎么想?他们和我们今天一样,是从满满的到震惊的范围吗?是否有人认为他们居住的整个陆地可能最终被淹没?他们对此做了什么?
你可能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线索。毕竟,由于大约6000年前大多数地方的冰后海平面停止上升,我们需要很久以前才能进入人们的脑海。
然而,这是可能的,因为在世界上长期存在的文化或多或少完整存在的几个地方,有些故事不仅回忆起冰后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 - 在少数几个地方 - 回忆起描述人们的回答。而这些在今天反映我们自己的程度是非凡的,为我们是否可以从远古祖先的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些故事中有哪些是什么?
从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北部出发,有土着原住民的故事,讲述现在大堡礁是干旱的土地,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发生在9960年前。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海洋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向陆上移动,驱使其居民在内陆。
20世纪30年代报道的一个Gungganyji故事指出,一个名叫Gunya(或Goonyah)的人对海平面显然不可阻挡的上升变得非常担心,他和他的一些人爬上了一座山,在山顶上他们发了一个大火他们加热巨石,然后将它们卷入上升的水域。据报道,这是“成功检查洪水”。
来自澳大利亚的其他土着故事回顾了人们如何应对海平面上升的现状,即现在的壮观的纳拉伯悬崖海底。由于担心“海水泛滥”将“蔓延到整个国家”,来自Andingari和Wiranggu人民的故事回忆起“各种鸟类女性”如何聚集密集的kurrajong根,并安排这些在悬崖底部形成一道屏障。
据说,这一行动“限制了迎面而来的水域”,从而阻止了“完全淹没国家”。来自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故事回忆起Wati Nyiinyii人如何“匆匆”到水边,他们迅速开始“捆绑成千上万根[木]矛以阻止侵入的水......这些捆绑堆得非常高,并设法容纳水”。
在这两个地方,冰后海平面在大约7000年前停止上升,这意味着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口头传递到今天。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东西,但它也迫使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毫不妥协地传承了近300代?
我们无法知道,但有理由认为,其目的是警告后代关于海洋表面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它在停止之前曾一度上升并淹没了大部分土地。这些故事的意图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描述,更像是为后代赋权的工具?如果是,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这些澳大利亚故事特别有趣的是,他们报告说人们的行为导致淹没停止,这表明这些故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7000年前,而实际上大陆边缘的淹没确实停止了; 这里的海面达到了目前的水平。
但世界各地并非如此。在欧洲西北部的许多沿海地区,海洋表面在数千年前并未稳定,但自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海洋表面或多或少地持续上升。似乎有可能在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的许多故事中埋藏着对此的古老记忆,表现为未能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
以布列塔尼的Ys和威尔士的Cantre'r Gwaelod等淹没城市的故事为例,这些城市与其他类型的城市一样,回想起现在在海底存在的“城市”,其精确的位置不确定。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个城市已经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可能已经从没有沿海防御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城市 - 相当精细的城市。
甚至允许一些细节的交叉,故事回忆起Ys和Cantre'r Gwaelod被围住的大门需要在潮汐高时被关闭;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归咎于这些城市的最终被淹没。原油估计表明,Ys和Cantre'r Gwaelod的淹没发生在8700多年前。
如果你认为这些论点牵强附会,那就考虑一下事实。在过去的一万年(甚至更多)中,人们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欧洲西北部,海平面一直在上升; 很明显,许多人一定是因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许多城镇曾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淹没。
为什么不应该保留这些深刻改变文化的事件的记忆呢?这不可能是因为记忆不能保存这么久; 他们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膝盖怀疑主义只源于我们的思想将古代故事重新塑造为具有事实基础的困难而不是我们被教导的有趣创作。
今天,正如7000,8000年以前的人们似乎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建立了对抗海平面上升的防御。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存在基于证据的科学解释,说明为什么海平面上升以及可能最好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海平面,更多的人信任世俗反应而不是七千年前的情况。
当时对当今世界的当代科学理解 - 正如他们今天为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 融合了世俗的反应(如建筑防御)和精神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知道几千年前的一些人可能会参与其中。
在布列塔尼的卡纳克(Carnac)采取石线,其中一些延伸数公里,涉及成千上万的竖石,曾被视为堕落战士的边界标记或纪念碑。在塞尔卡森的想法是,这些石线表示打算阻止海平面上升莫尔比昂湾的灾难性影响,6000年前的物理和形而上世界之间的“认知障碍”是什么,我们正在学习其他地方保持。
例如,沿着许多北海欧洲海岸,整齐排列的曾经有价值的物品,如石器,甚至人类遗骸,可能是故意创造的,作为祭祀神灵以阻止海洋的崛起。坟场可能故意位于沿海地区,象征性地将它们稳定在当地人民的心中。来自塞尔维亚Lepenski Vir的鱼神砂岩雕塑可能是用来防止淹没的图腾。
即使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侵占海洋无用的物理障碍也可能已成为象征性的障碍; 弗朗西斯·普赖尔(Francis Pryor)以这种方式解释了英国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附近的弗兰芬(Flag Fen)木结构的一个例子。
在一个全球联系的世界中,像气候变化这样的人类挑战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全球性问题 - 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理解和框架,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这听起来有什么问题,我听到你说了吗?
实际上相当多,尤其是因为全球立场不加批判地对西方科学的理解赋予特权,并使其他人的理解下属,包括我在Vabea的朋友努力理解海平面上升作为上帝的旨意。
气候科学家目前正在广泛认可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气候变化减缓最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决,但考虑到受影响人群和环境并置所代表的多种多样的情况,适应性更好地在当地得到解决。
默认情况下,这是人们7000年前的位置。世界各地都承认没有一个解释为什么海平面上升。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使他们的观察合理化,而这些反过来会决定他们的反应。
想象一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想象一下,如果7000年前英国芬兰地区或澳大利亚Nullarbor受影响的人感到无法在没有国家当局指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是否会有人跋涉数周或数月甚至数年来寻求这个方向,只是被一个不熟悉当地背景的人告知完全没用的东西?
想象一下,如果国王在听到他遥远的臣民的两难困境时,下令在他的形象中竖立一座雕像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他的人民做了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呢?
因此,我们可以从关于人们对海平面上升的反应的古老故事中得到一个教训 - 至少是有效的反应 - 是了解当地环境最佳的当地居民最适合设计和推动适应性解决方案。不可避免的是,随着适应性决策在地理上变得更加遥远和更加自上而下,它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搜索古代故事,以了解我们如何最好地应对当代气候变化。
我对澳大利亚关于人们如何担心海洋可能在整个陆地上升的故事以及一些采取的措施中隐含的绝望感到着迷。显然,Gunya爬上山并不是一个长期考虑的解决方案,正如Wati Nyiinyii“匆忙”建造他们的悬崖脚栅栏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考虑的方法。
所以也许就像今天一样,那些在这些社会中掌权的人们已经猖獗; 也许他们否认了他们自己眼睛的证据,因为他们认识到它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许采取基层行动,与罢工学童的现代抗议相比,推动变革。
从Ys和Cantre'r Gwaelod这些古老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更为明确的教训,即长期的海平面上升可以暂时抵制 - 用现代术语,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海岸或适应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放弃易受伤害的地方并占据较少暴露的其他地方实际上更为圣人。
这是现代气候变化科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说服沿海居民临时修复不会持续,而且转型变革无论多么痛苦,都是唯一可持续的未来选择。
我在Vabea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他在附近的Narikoso的亲戚将成为第一批搬迁到更高位置的斐济社区之一。他担心Vabea不会落后。他抱怨不可避免的破坏的严重性,但也感谢上帝,他的家在一个高岛上,至少有一些地方可以撤退。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太阳消失在遥远的山丘后面。然后出乎意料的是,他以一声巨大的狂笑打破了晚上的安静:“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开始大笑 然后他解释道。
“我的祖父,”他回忆说,“他总是说,他的祖父永远都说我们的人民搬到海岸是个错误。那是一个我们住在山上,远离海浪的时代,但随后你们有人来到“ - 他给我,外国人,一个虚假的眩光 - ”并迫使我们一直到水边。
“旧的,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说不去,但我们别无选择。在这里,我们和dina saraga - 太真实 - 我们现在发现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应该听听过去。












